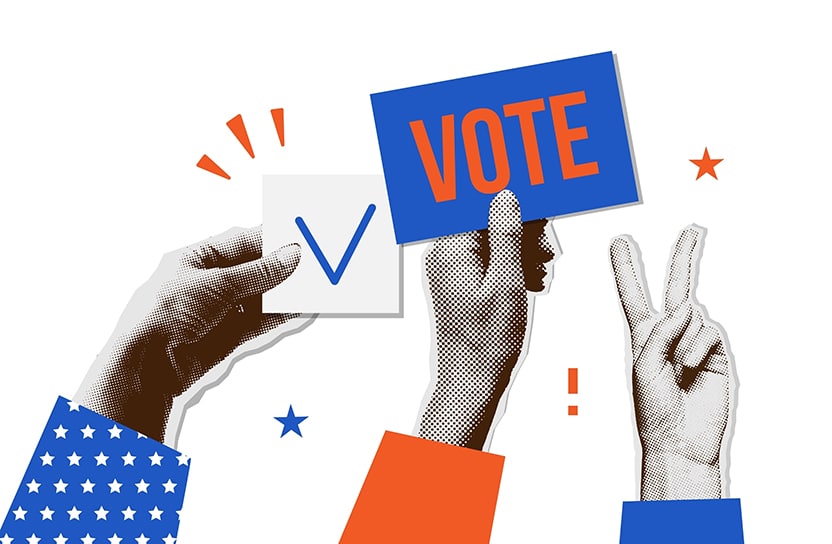撰文/李念祖(東吳大學法研所兼任教授)
公民投票結果拘束代議政治的議會嗎?這是本篇討論的主題。
民主政治,主權在民,真正的意思是什麼呢?最素樸的道理是,具有正當性的統治者不是天子、不是皇帝、不是國王,也不是政黨,甚至不是政府;人民才是具有正當性的終極統治者。終極的統治者,如何展現其統治權威呢?答案是,以誰才擁有立法的正當性為準。
不同的民主國家,誰掌握立法權?正確答案可能還有些微的差異。最老牌的民主憲政國家是英國,歷經了數百年,發展出一個人民成功地將國王的權力剝奪殆盡的政治體制。1689年的光榮革命,原本的國王主權轉變成為國會主權(或也稱為巴列門主權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立法權歸屬於國會,國王也要遵從法律;每位國會議員都是選區選民的民意代表,所有的法律都必須出自國會;立法權是單一的來源,國會主權就是主權在民的具體實現。這是民主政治代議政體的原型。
美國13州殖民地因為不滿英國民主國會的欺凌而獨立,不立國王而立憲法典加以取代,成為建國的基石。憲法中創造了兩個民選的兩院制國會,又創造了一個透過選舉人團產生的民選總統,用民主來制衡民主。英國所無的一項發明,是憲法典既非由國會所制定,也非國會所能自行修改者;反而國會是由憲法所創設的,這稱為剛性憲法,國會立法的權限來自於憲法,立法不能牴觸憲法。
剛性憲法的修正程序,各國規定並不相同。我國也是剛性憲法國家。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修憲程序應先由立法院通過提出修憲案,再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有效同意票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即通過之。」根本大法修正時的立法者不只是代議士,還有人民自己。剛性憲法的出現,與英國國會主權的政體模型,非無差異,值得再從公民投票與國會立法之關係進行觀察。
由於實際上的困難明顯,民主國家的主權者固然是人民,但即使資訊工具發達已進入人手一機的網路時代,一個國家中有待立法決定的事項多如牛毛,亦不可能事事均交由公民投票表決定奪。最困難的所在,還不止是有待票決的事務數量浩繁,而是投票之前,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討論審議程序,很難在全體公民之間真正開展進行,一椿法案在議會中應循會議程序進行所必不可少的種種細節,包括提案、附議、與會者充分參與討論、修正、再修正、付委、程序動議⋯等等,均無從交由數以百萬千萬計的選民同時集體參與且依序進行 。
此中根本的道理在於,所有代議士在議會程序中待為之事,如果均由全體選民親自為之,那就是人人都必須成為鎮日舉行會議的專業代議士,千萬人組成的議會踐行審議民主的正當程序,因為必受時間及物理環境的限制,勢有難能。此之所以公民投票可以決定的事項極其有限之故。
又由於民主決策的品質良窳,其實取決於討論的程序是否經過充分討論的深思熟慮,而非取決於決策的內容是否正確。因為決策內容的正確與否在民主政治中必是見仁見智,永無定論,才須於議會中不能取得共識時交由投票決定。科學問題,比如水的化學結構是否為H2O,就不是該由民主的投票程序加以決定的事項。在動態的社會生活中,很難確保公民投票的選民均能充分了解主旨議題而於深思熟慮之後做成決策。實際的政治社會場景中,很難期待公民投票會比議會通過決策品質更為精緻。
就是因為這層道理,在英國是否交付公民投票也要先經國會決定;國會決定交付公民投票的例子並不常見。值得注意的是,公民投票的結果,仍然需要再回到國會另行制定、通過法律加以實現。因為是國會主權,國會代表人民,是唯一的立法者。譬如那年英國考慮是否脫歐,國會決定交付公投;公投結果決定脫歐,仍然要回到國會立法才能作數。這稱為法治的正當程序。
更值得注意的是,從法律制度上言,公民投票的結果不是法律,國會立法才是,制度上英國國會如何立法並不當然須受公投結果拘束。但是事實上當公民投票結果需要進入國會進行立法的時候,即使當時的執政黨並不贊成脫歐,也沒有挾其人數優勢使用法律阻擋脫歐,反而是通過了盡可能體現民意的立法,最後實現了公投的脫歐決定。背後的道理,是因為國會議員作為民意代表,政治信念是不該以己意為民意,而是應該以民意為己意。這事屬於政治性的決定,民意對於議員若是具有強大的政治倫理拘束力,自行其是的議員就會在下次選舉時面臨選民的制裁。這就是民主精神的真實展現!
我國憲法上規定主權在民(第2條)人民有創制、複決的直接民權(第17條);同時規定:「創制複決兩權之行使,以法律定之。」(第136條)也就交由立法院制定法律促成人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行使直接民權。立法院也因此制定了《公民投票法》,其中包含了全國性與地方性的創制複決。一共分為三類:法律(或地方自治條例)之複決,立法原則(或地方自治條例立法原則)之創制,與重大政策(或地方自治事項重大政策)之創制複決(第2條)。
簡單講,「法律之複決」是要否定既定的法律或法條規定;複決通過,就是人民不同意民意代表所寫的法律。公民投票法於是規定,法律複決案一旦通過,於公告公民投票結果之後三天,被複決的法律自動「失其效力」(第30條)。這是立法院決定人民的複決決定直接發生法的拘束力。不是因為議會主權,而是因為主權在民。
創制法律,則因為公民投票不能回應需經動態的正當程序始能立法的程序需求,依公民投票法乃只能由選民創制立法原則而不是法律本身,也就還須要議會發動立法程序,寫成法律以充分實現公投通過的立法原則(第30條)。公民行使的是創制權而非立法權;乃必須由掌理立法權的議會通過立法完成法律程序。
然而,議會可以拒絕依照公投通過的立法原則立法嗎?依公民投票法規定,立法院必須寫成法律加以實施(第30條)。但如何確保議會遵守此項規定呢?那就和英國一樣,要靠人民於下次選舉時讓不服膺民意的代表落選。富有智慧而思有效控制議會中民意代表的選民,就該懂要如何善用手中的選票,使得民意代不敢陽奉陰違、藉故拖延、甚或明目張膽地違背業已經由公民投票所表達的民意。
至於重大政策的創制,依照公民投票法規定,與法律原則的創制道理相同。包括立法在內各政府機關部門,雖然仍是各自行使職權,但仍然必須盡其所能,運用職權促成公投通過的重大政策落實施行。從政治倫理的層面說,只有選民懂得要在下次選舉中發揮影響力,使用選票使得欲與民意背道而馳的議員落選,才能防止民意代表敢於背棄選民。
一言以蔽之,議會主權的國度,議會也需要奉行政治倫理盡力實質實現不具法律約束力的公民投票結果,以求符合民意政治的真精神。何况是在主權在民的國度,無論從法律制度上或是政治倫理上說,議會更無違背公民投票的結果自行其事的餘地。